
新闻中心-
青海之美,是高原之美,是山峦棱角分明的素描,是湖水蓝绿退晕的渲染,是生灵自由不羁的灵动。
青海之美,也是人民之美,唯有这高原之美,才能在广阔的野性中孕育出青海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和自然质朴的生活。
青海之美,还是工业遗产之美。就在大通705厂那已经荒芜但还存有大体量构造的工业遗产当中,我似乎还能感受到三线建设时青海工人们对国家建设、对生活、对未来的豪迈情怀。
不论高原之美、人民之美还是遗产之美,这些无可复制的魅力无一不是时间的连续积淀所形成的。被青海之美所感动,更要为守护青海之美而努力。
——摘自2014年青海705厂工业遗产保护设计营同济学生黄瓒的感言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为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建设工业基地。青海的军事工业、核工业以52、56、221、701、704、705、706、805、806、535 等工厂为代表,这些企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实验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三线”军工遗产。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三线建设的结束,上世纪90年代大批“三线”军工厂面临转产改制或倒闭破产,昔日厂房处于弃置状态。这些承载着几代人梦想、奋斗和记忆的历史空间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中逐渐被人遗忘,亟待抢救性保护与再利用。
青海光明化工厂(代号705)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坐落于青海大通县老爷山脚下的昔日“三线”军工企业虽已倒闭荒废多年,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显赫是护国战功。为了应对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 705厂集当时国家最强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于1965年而建,由化工部直接管理,为中国核武器生产提供自主研发的重水原料,改变了之前重水全依赖苏联进口的局面。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随着我国加入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对重水产品实行了限产和关停政策,国家计委1985年发函明确提出转产民品问题。705厂先后贷款数千万元建设了6条民品线,却连年亏损。工厂开始限减产,80年代末关闭了重水生产线,报废了生产装置,国家将生产重水的基地转移到四川泸州火炬化工厂,1996年705厂正式宣告破产。
感叹命运的安排如此神奇,将远在东海之滨上海的我与辽阔壮美的青海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纽带就是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青海705厂成为这个纽带上的重要触媒。自2013年第一次走进705厂至今已过去整整7年,而正是这个厂引发了我们对共和国这段“三线”建设历史的了解,展开了对“三线”工业遗产价值的认知及其保护利用的研究,也结交了当地几位为保卫这段国家记忆和工业遗存而默默奉献一生的守护英雄。705厂开启了我们对“三线”工业遗产研究和保护之路,大致走过了3个阶段:
1. 2012-2014 705厂前期宣传和保护启动
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为青海当地政府宣传705厂的遗产保护价值,并通过公共讲座、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圆桌会议及联合国内几家著名高校师生赴青海当地举办工业遗产保护设计营等方式来推进社会民众对705厂的价值认知和未来转型的思考。最初的起因是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青海专委会杨来申主任于2012年底向青海省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705厂去留问题的提案——《青海工业文化博览园策划建议书》,打响了青海705厂保护战的第一枪。接着2013年11月由他和蒲仪军博士的引荐,我与日本建筑师学会前会长乔治国广教授受邀第一次前往青海大通,为当地县政府各级领导和西宁师生举办了一场工业遗产保护和再生大型论坛,县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了县常委宣传部孙桂萍来主持演讲,与会者300多人,会场反响热烈,大家对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这个理念都感到新鲜和振奋。


为了进一步推动705厂的转型和盘活,2014年7月我与杨主任共同策划联合大通县政府举办了针对705厂保护和再生的设计工作营,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集聚大通,在短短的8天时间里在厂区展开现场记录和调研,并根据当地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特点为政府出谋划策。设计营期间,学者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开展了圆桌会议,充分交流和讨论这些军工企业存在的现状问题、保护困境、发展政策及前景,对705厂的历史地位和再生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设计营最后为韩县长汇报,为政府提供了5组视角不同而富有创意的再生设计策略,圆满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设计营的成功举办意义深远,无论在规模、方式、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在青海历史上尚属首次,为推动青海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次设计营得以顺利举办离不开各方的支持和帮助。我和杨来申主任各有分工,我负责高校联络、营员组织和专业安排,杨主任团队负责所有师生在当地的食宿和交通、工作场地安排及对接政府落实资金。杨主任热情好客、侠胆义肠,其手下的刘芸善解人意,耐心细致,负责设计营全部师生的食宿和交通等后勤工作,尽力保障设计营的有序展开,此外蒲仪军博士也分担了部分设计营后勤联络和接待工作。
设计营得到了青海省大通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韩生才县长、孔佑鹏副县长、何斌副县长、孙桂萍宣传部长等都先后参与听取了师生的汇报,给予我们工作上的便利和资金支持;青海省政府参事、原住建厅副厅长李群、住建厅总工程师熊士泊以及青海省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王涛非常关注设计营的动态,他们全程参加了开营和闭营活动,李群参事积极组织省级建设、文史、文物、规划、大通县领导、705厂等在内的相关部门领导与学者座谈研讨,包括青海省文史馆名誉馆长谢佐、西宁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廖坤、西宁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曾永丰、省经信委材料工业处处长袁荣梅、黎明化工厂军品部长单正军、大通县东部新城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马云及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朱树新等其他嘉宾。谢佐馆长文史渊博,在晚餐上即兴作赋一首:
老爷山下苏木莲,文化走廊经北川。
诸君来青保遗址,再生蓝图步前贤。
莫道破产七零五,老爷娘娘二名山。
鹞子沟与察汗河,诸君功成衣锦还。
设计营最后的方案汇报会邀请到同济大学《时代建筑》杂志主编支文军教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李昕主任两位与会做出点评和指导,青海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陈柏昆院长和韩秀茹老师为设计营的老师专家提供了学术论坛的场地,此外全程协助设计营交通服务的西宁光影野外科考服务公司张炳宏以及青海省土木建筑学会、青海省勘察设计协会、青海省房地产业协会以及新华社驻青海记者站、央视驻青海记者站、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网、西宁广播电视台、西宁晚报等多家媒体给予了设计营支持和宣传。
参加本次设计营的高校师生和学者都非常重视和投入,毕竟到大西北偏远地区的青海来做实地调研机会难得,加上705厂是国内比较罕见的“三线”军工遗存,所以整个8天的设计安排紧凑高效,短短的几天里完成测绘调研、中期汇报、小组讨论、熬夜绘图到最后汇报,大家忘我的工作和辛苦付出最终为当地政府带来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和设计策略。
参加的师生有清华大学刘伯英副教授和许懋彦教授以及学生董笑笑、蔡长泽、张之洋,天津大学的徐苏斌教授及学生张家浩、张雨奇,东南大学的董卫教授及学生马建辉、任佳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周立军教授及学生刘晓丹,同济大学参加的4位老师分别是:规划系张松教授与学生黄瓒、张萌,建筑系朱晓明教授与学生田国华、陆地副教授与学生胡鸿源,陈易老师的学生蔡少敏以及我和我的3位研究生——姜新璐、刘春瑶、叶长义,兰州商学院的苏谦副教授及学生姜珍珍、苏子聪,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王刚老师及学生李青青、万马仁青、王浩、田启晶。全部师生分成5个设计组和1个记录组。





设计营的举办因事先准备充分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清华大学的刘伯英老师认为大家想象力非常丰富,他和许老师带领的小组策划将此厂转型为反恐特警的培训基地,尽量避免与他组雷同。“我觉得这次设计营的主要意义是给大通留下一些好的想法,帮助大通能够下决心把705厂作为一个工业遗产保留下来,了解它的价值,对它今后的再利用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并不在于我们设计有多深入”,同济大学的张松老师认为此次设计营把学校打散后分组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方式,大家在一起开展调查和设计方案讨论,彼此的交流可以深入一些,徐苏斌老师则认为这次设计营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跨学科、多角度的尝试和探索,陆地老师将工业遗产的粗犷美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技术工业美、原生的美,“这种时光美的确对任何人都有效,即便没有任何的历史文化功底一样能够打动你。”
天津大学的张家浩彼时加入设计营的身份是新博士生,如今他早已博士毕业并在高校成为一名教师,研究方向仍然是延续导师徐苏斌老师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他虽以往参与导师课题也调研过一些工厂,但705厂涉及的核工业、军工厂的身份透着一种神秘,牢牢吸引着他,“我们组在概念方案的试图通过工厂本身具有的神秘特质与基地特性,将农业景观旅游、军工探秘、休闲娱乐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多种业态进行复合,打造多元化的、既与保护工业遗产不违背又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保护模式。”他后来回忆道。
学生们来自不同城市和学校,虽然相处短暂,但彼此真诚的交流和协同奋战使学生们不仅提高了专业能力,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生刘春瑶入营时还是同济一名准硕士生,如今她将很快获得美国建筑遗产方向的博士学位。她回忆道“这里面有的人成了我最亲的同学、有的人成了我的室友、有的人成了旅行的伙伴、而不在身边的人在偶尔跨国遥远的距离发发信息点点赞,人虽远情不减”。正如杨来申主任说的那样,经过老师和同学们不懈的努力,人们从原来的不明白、不支持、不理解转变为支持和赞赏,并理解我们活动的意义了,就这一点我们工作没有白做,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2. 2014-2017 705厂专著出版
2016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许健主任联系约我书稿,我便萌生了要将705厂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编写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以及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的关注。在许主任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联合同事朱晓明教授和杨来申主任一起共同完成此工作。作为2014年705厂设计营主要策划和组织者,我和团队记录了设计营的全部进展过程和终期汇报方案,而这部分内容将构成此书的核心内容,此外“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和评价由朱老师梳理,而原厂领导、技术人员等口述访谈则由杨主任负责落实。这本”三线”著作以705厂为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许主任的努力下于2017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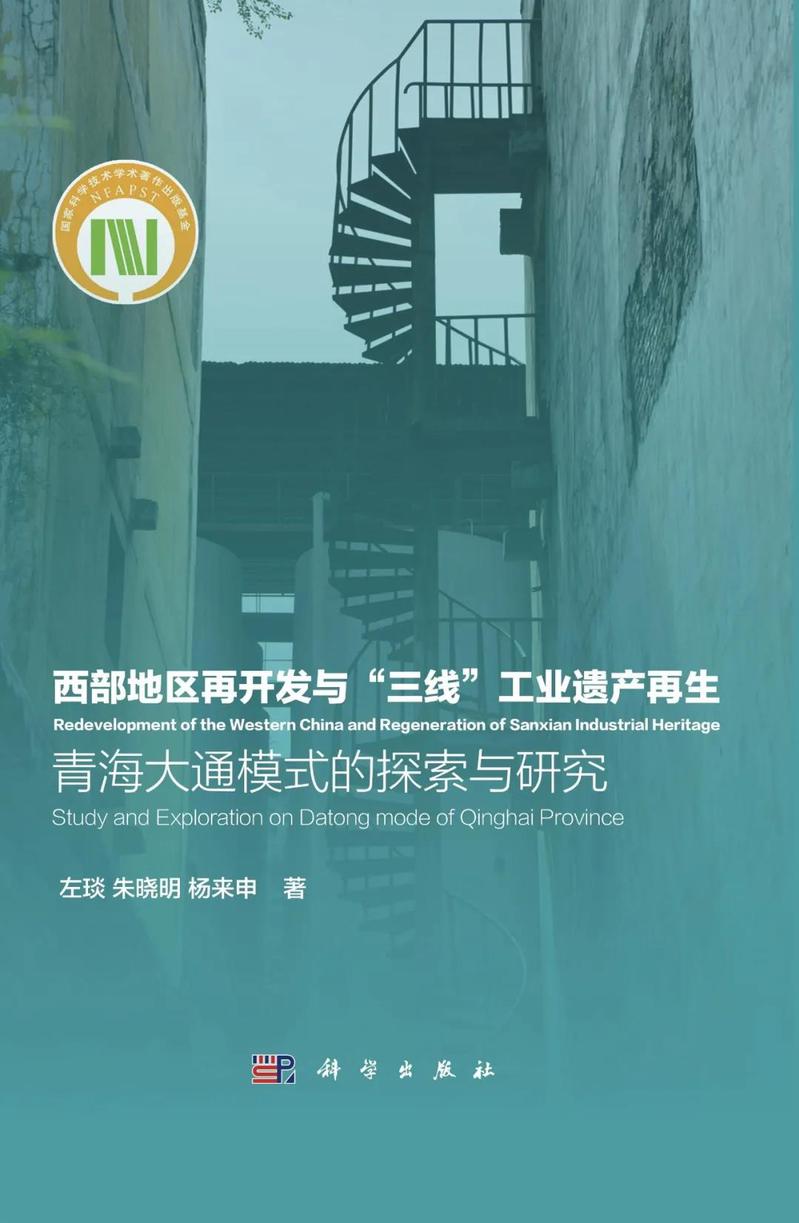
此书以2014年设计营的成果为基础,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增加了青海“三线”特别是化工历史的梳理以及705厂的建厂历史背景,并借鉴国外冷战遗产保护的经验来探索“三线”工业遗产的未来出路。时隔两年多,我在整理设计营资料时一直在思考如何看待这次设计营的意义,如何看待705厂这些残垣断瓦背后更深层的价值。直到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女排勇夺金牌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它就是一种新时空下的新“三线”建设。如果说当年是从内地带着设备技术和人才去支援边疆,是物质、有形的支援,那2014年的工业遗产再生设计营是沿海和大城市的教学科研力量以及口述史访谈是带着新思想和观念去支援的,是无形和精神上的支援。在写作中,我越来越清楚编写本书的意义和担当,是要把青海“三线”精神找回来,把环境和事件背后所蕴含的“两弹一星”精神找回来并传承下去。工厂遗址活态化保存只是一种手段和方式,重要的是给曾经燃烧过青春和热血的一代人及他们的后代一个说法,给政府一个参考,给社会大众一个重温历史的载体。挖掘和总结“三线”历史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代人的奋斗精神,就像女排精神的回归是制胜法宝,这是当前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也是重铸伟大中国梦的信仰基础。
本书邀请到两位重要人物写序,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和青海省原住建厅李群副厅长。作为省政府参事的李厅长在序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把相距西宁市百公里之外的海晏221厂和核爆轰试验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有否想过这个距西宁40km的705厂也是当时核工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曾为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出过大力做过巨大牺牲?”他站在青海省核工业发展的角度对705厂的历史价值做了高度肯定,为705厂的身份认定推波助澜。
本书专门辟出一章记录了对705厂光明人的访谈,这也表明了我们作者对于环境和人一起保护的立场和态度。“记忆是当下鲜活的情感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有选择的、批判性的重构。属于集体的记忆既是个体碎片的叠合,更是有甄别的传承,这些记忆也必然影响了后代个体,用以观照现实。试图构筑一部整体的705厂史无疑极为困难乃至无法实现,705厂的记忆不过是从中采撷了一些碎片而已,但倘若能从中理解光明人的内在精神,研究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摘自书中(P202)

705厂原职工分成第一代和第二代光明人,他们差不多都是随着大中型化工企业移民来此的职工、徒工、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孩子们长大后也基本进厂,延续成为企业的一代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直至1996年705厂破产。被访谈者长者近九旬,年青的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他们个人的经历分别横跨了中苏友好、“三线”建设、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高考求学、下岗买断、突围青海等关键阶段,职业上分为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两类,基本能反映705厂的运转特征。先后接受我们访谈的有1956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苏维埃工程学院化工系无机专业、曾任705厂革委会生产组组长的90高龄老人洪小灵、原705厂厂办主任王斌(2016年去世)及原705厂供气208车间工人的王斌妻子、原705厂仪表车间工人谢萍、曾任705厂化验室实验员和司机的“光明帮”群主邹国兴、原705厂子弟学校教师光明二代的杨春生、原为705厂1车间工人的光明二代李长平、原705厂供销科副科长王松岐、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原705厂科技开发科科长纪子博、原705厂长许存武以及刘志新、于和生等,这份无形的精神遗产将作为历史档案保存给后代子孙,让他们铭记过去。
我的研究生刘春瑶、姜新璐、张飞武、程城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收集和整理资料、翻译美国冷战遗产报告、整理和绘制部分插图、后期视频制作等,在他们的协助下,本书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

3.2017-2020持续关注705厂动态
2017年为配合新书出版,我们特别在上海和青海西宁两地组织了两场新书发布和交流会。第一场依托同济丰富的专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在学界和设计圈里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和研讨会,得到了同济大学《时代建筑》编辑戴春老师负责策划的“Let’talk”平台的支持和宣传。到会者包括了学者专家、设计师和在校学生40多人,除了我和朱晓明老师作为本书作者外,还邀请了曾参与设计营的同济陆地老师以及著名出版人和城市批评家王国伟老师等与会座谈,学术氛围浓厚。我们对于时间和地点做了精心安排,选取了2017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个特殊日子,并将活动举办地安排在由老厂房成功改造的同济大学明星建筑师也是我领导章明教授的原作设计公司,环境与新书主题非常贴合,也令每个到访者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第二场新书发布会于7月7日在西宁市中心一个环境清幽古朴的茶室空间里举行。我和同济大学《建筑遗产》杂志编辑蒲仪军老师带着研究生程城又一次来到青海。与会者包括社会各界代表,有青海文化名片谢佐先生、清华大学的刘伯英老师、青海省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王涛以及宋贵宾秘书长,705厂光明人代表纪子博、杨春生、马应孝、王国柱、李长平,青海建筑职业学院王刚和马贵老师、青海大学应全杰老师,西宁市委党校领导、青海监狱文化博物馆李成清馆长及柳安智科长、兰州赞助商张明娟经理等,青海日报记者作为媒体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者畅所欲言,交流看法,将工业遗产保护上升为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来看待,很快达成了一种共识。
趁这次在青海举办新书发布会之际,刘伯英老师、705厂原技术人员纪子博、杨主任、蒲老师以及我和程城一行人又来到705厂参观,相隔3年后又故地重游,心绪万千。除了主大道边的野草比以前长得更茂盛外,整个厂区与3年前相比变化不大,依然静默荒凉。庆幸的是这些建筑没有被拆除,它们静静地老去,无奈地等待着它们未知的未来。我们此次带了无人机将整个主厂区和两个附属厂航拍了一遍,回沪后剪辑完成了一个6分钟的视频于我所在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网站上正式发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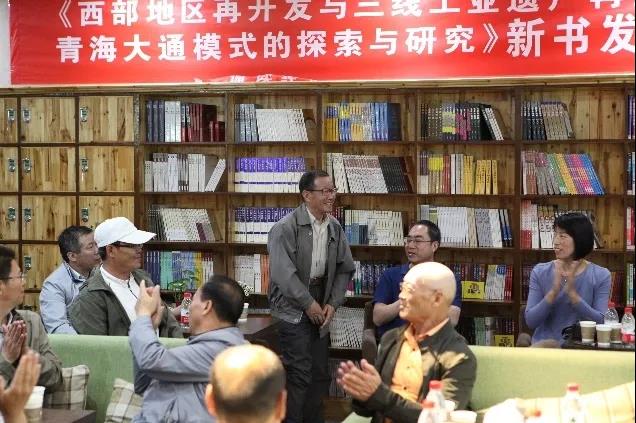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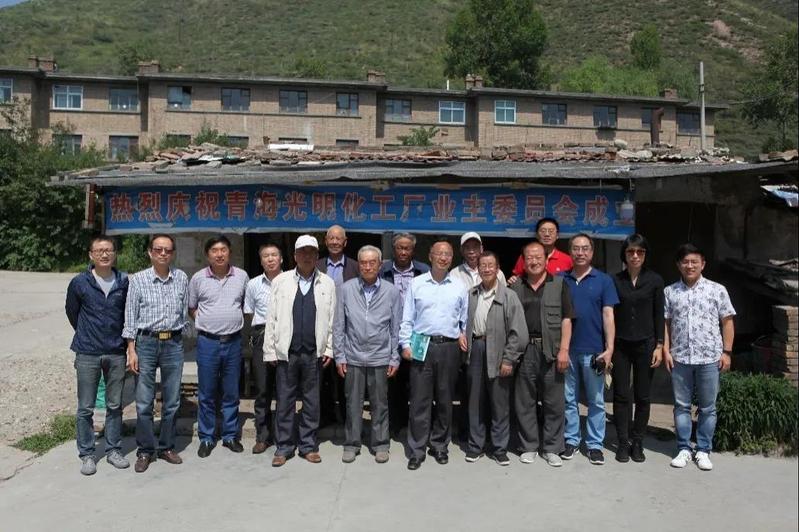
2017年11月我邀请了杨主任、纪子博一起与我和程城参加在贵州省遵义市1964文化创意园举办的中国“三线”遗址与旅游开发研讨会,会上我介绍了705厂的研究成果和新书出版情况,并在会场播放了705厂的视频,向中国三线研究会的王春才会长、何民权部长等几位领导以及中国社科院陈东林研究员等介绍青海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被采访的705厂光明二代杨春老师在西宁新书发布会后成为我青海又一个真挚的朋友。他很小就随父母迁居青海705厂,后为705厂子弟学校教师。父亲正当壮年时因公殉职,年仅40岁。作为705厂二代,他的命运和705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现年58岁的他经历了705厂的破产倒闭、改制转产、废弃破败的悲惨历程,他近些年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渠道向青海省有关部门递交提案,2018年为抢救性开展青海“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利用的提案与省发改委、省文化旅游厅、国资委督促落实。在这几年中,他曾三次向青海省经信委(现工信厅)提交工业遗产保护申请,但都未被批准。2019年又向青海省国资委提交了一份705厂详实的产权变更说明,希望省政府能重视并妥善解决705厂全体留守人员的安置问题。当获悉2020年9月第四批工业遗产核查组前往705厂核查时,杨老师作为原厂职工为核查组专家详细介绍了工厂历史和原建筑功能,令他们不虚此行,了解了705厂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实情。此次705厂能否获批第四批工业遗产名录未得知,但其作为青海核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得到了核查组专家的一致认可。
在杨春生老师的引荐下,我于2018年认识了青海原子城(221基地)的核二代梁益福老师,也有幸和他成为好朋友。705厂与221基地关系密切,后者的中子源制造所用的重水就是由705厂供应,因此705厂与221基地一起共同构建了青海核工业生产链,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梁老师和杨春生境况相似,也是从小随父母来到青海,在221基地一分厂102车间工作,从事核武器核心铀部件加工。自 2016年开始梁老师自费在全国采访核一代老人,挖掘和整理221基地的历史文化,与同为221基地工作的徐金环老师一起打造了全国公益平台《梁子故事》,发布了相关文章和文献资料500余万字,策划创作的3集纪录片《代号221》于2019年9月在央视九套及全国各电视台播放,尽自己的全力将核工业建设二代人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弘扬下去。2019年我和学生程城与杨主任、杨老师一起又一次去了原子城,在梁、徐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221基地几个厂区和生活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705厂,这个在冷战时期应运而生的国防军工厂像一个叱诧风云的前朝老将军,骄傲地婆娑着胸前的勋章,在和平年代却因国家产业调整和体制改革等因素倒在自己的国土上,令人扼腕叹息。尽管历史已翻过了一页,但身可倒,魂犹存。前辈们在国家危急时刻毅然赶赴西部建设边疆,不畏艰难困苦,为国家的安宁和富强做出了伟大的奉献,这种崇高的品质就是国家提倡发扬光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们被深深打动了,它促使我们站出来,有义务和责任去为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工业遗存而奔走呐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的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
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
最后向所有顶天立地、无私无畏、经历过“三线”建设岁月的高尚灵魂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学院介绍
学院介绍




